百年前無藥可醫 菌血症與作曲家馬勒之死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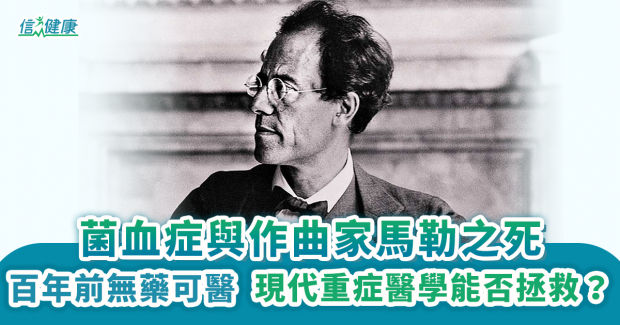
提到馬勒(Gustav Mahler,1860-1911)的音樂,大家腦海浮現的都是規模龐大、編制複雜的管弦樂作品。我家珍藏蕭堤爵士指揮芝加哥交響樂團的馬勒第一號交響曲《巨人》,其中第四樂章那種「打破黑暗、邁向光明」的感覺,是每次考試前最愛聽的音樂。作為跨越二十世紀後浪漫時期作曲家,馬勒的死因有可靠紀錄,是典型嚴重感染個案:心內膜炎;細菌可能進入血液形成「菌血症」。
奧地利著名作曲家馬勒,一生與病痛糾纏不休。根據漢斯約阿希姆特拉普(Hans-Joachim Trappe)教授在醫學期刊Med Klin Intensivmed Notfmed發表的研究,馬勒常年飽受反覆發作的扁桃體炎、痔瘡等疾病困擾;這些看似不相關的病症,實則為他的健康危機埋下致命伏筆。1907年,馬勒的4歲愛女病逝,他本人也被診斷患有「二尖瓣缺損」,表示他的左心房與左心室之間的瓣膜無法完全緊閉,導致血液逆流,心臟須更費力地工作;在當時,這是一個無法治癒的病症,對這位正處於創作巔峰的藝術家造成沉重打擊。

然而,在1911年奪走馬勒生命的疾病是「細菌性心內膜炎」。要理解這個疾病,必須深入探究其病理機制;心內膜炎,顧名思義是心臟內膜(特別是心瓣膜)發炎感染,在馬勒的案例中,病原體是口腔常見的鏈球菌(Streptococcus)。人體血液循環系統本應無菌,但當身體其他部位出現感染,例如馬勒反覆罹患的扁桃體炎,或接受牙科治療,甚至因痔瘡出血,細菌都有可能突破防線,進入血液循環,形成所謂的「菌血症」(Bacteraemia)。
對於健康的心臟,短暫菌血症不會造成嚴重後果,免疫系統能將其清除。然而,對於像馬勒這種有二尖瓣缺損的患者,情況截然不同;受損或異常的心瓣膜表面往往較粗糙,血流經過時容易產生湍流,為細菌的附着與定居提供絕佳溫床。當細菌附在瓣膜,便會開始大量繁殖,並與血液中的血小板、纖維蛋白等物質結合,形成一團脆弱、菜花狀的贅生物,正是心內膜炎所有災難性後果的根源。
首先,贅生物會進一步破壞瓣膜的結構,導致瓣膜功能嚴重失效,引發嚴重心力衰竭,患者會出現呼吸困難、水腫等症狀;其次,贅生物非常脆弱,碎片會隨時脫落,隨血液流向全身各處,造成器官栓塞。栓塞到大腦會引發中風,到腎臟會導致血尿與腎功能損傷,栓塞到皮膚則會出現瘀點或疼痛的小結節;此外,持續的感染會導致患者出現發燒、畏寒、盜汗、貧血等全身性中毒症狀。在二十世紀初,沒有抗生素的年代,感染性心內膜炎幾乎是百分之百的致死性疾病,醫生對此束手無策,只能眼睜睜看着患者因心力衰竭、中風或敗血性休克而走向死亡。
馬勒的病程正是這一經典病理過程的寫照。1911年2月,他在紐約因嚴重的咽喉感染發高燒,健康急轉直下。儘管他隨後返回維也納尋求當時最好的醫療照護,但病情已回天乏術。鏈球菌在他的二尖瓣上肆虐,摧毀本已脆弱的心臟功能。他於1911年5月18日與世長辭,留下的第十號交響曲手稿,成了他未完成的絕響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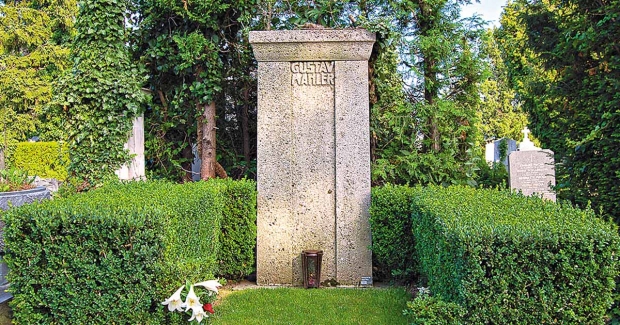
現代手術能治
現代重症醫學能否拯救馬勒?若他生於今時今日,命運將截然不同。首先,現代醫學對風濕熱(一種由鏈球菌感染引起的自體免疫疾病,可能損害心瓣膜)的有效防治,或許能從根本上避免發展出二尖瓣缺損。即便瓣膜問題已存在,現今的「感染性心內膜炎預防性抗生素用藥指南」,會建議他做任何可能導致菌血症的醫療程序(如牙科治療)前服用抗生素,降低感染風險。萬一不幸感染,高解析度的心臟超音波能清晰發現瓣膜上的贅生物,確立診斷。透過數周靜脈注射抗生素治療,足以徹底清除深植於心內膜的細菌;若瓣膜已被嚴重破壞,藥物難以控制心衰竭,心臟外科手術可進行瓣膜修補或置換,直接移除受感染源頭,挽救生命。這些技術在1911年都是天方夜譚。
馬勒的故事不僅是音樂史上的哀歌,更是一個強而有力的醫學案例。當我們聆聽馬勒交響曲中那些關於生命、死亡與救贖的樂韻時,也不禁感嘆生命的脆弱。
撰文: 王建芳醫生_臨床微生物及感染學專科醫生
[信健康] 淺談名作曲家菌血症死,醫生資訊可留意!【更多健康資訊:health.hkej.com】
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