感染霍亂? 因同性戀壓力自殺? 探索柴可夫斯基死因之謎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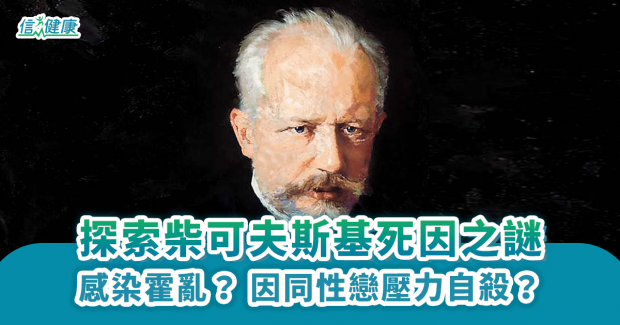
我家孩子最熟悉的古典音樂家,並非巴哈、莫扎特、貝多芬或蕭邦,而是寫作經典芭蕾舞音樂的柴可夫斯基(1840-1893),他的《胡桃夾子》是每年聖誕節都會選播的曲目,而《天鵝湖》裏的《四小天鵝舞曲》更是我兒子最愛,每次一聽到就會模仿舞者的舞步,非常惹笑。
然而,柴可夫斯基的死因至今仍是一個謎團。1893年11月6日,這位偉大的俄羅斯作曲家在他的《第六交響曲「悲愴」》首演後僅9天去世,享年53歲。當時的醫生與官方紀錄都宣稱他死於霍亂,但這說法從一開始就受到質疑,也有些線索令人懷疑這可能並非真相。
根據官方紀錄,柴可夫斯基的死亡過程很簡單。他在聖彼得堡一高級餐廳用餐時,飲了一杯未經煮沸的水,幾天後便因霍亂去世。霍亂由霍亂弧菌引致,病人因飲用受污染的水源或食物而出現急性腸道感染,病徵包括嚴重腹瀉和嘔吐,病人或會因嚴重缺水而死亡。
現在,霍亂主要影響居住環境差、衞生環境惡劣、政局不穩的地區,例如海地在2010年地震後一度爆發霍亂疫情;雖然在柴可夫斯基身處的十九世紀,人類才剛認知到微生物為傳染病的致病源,衞生基礎建設仍嚴重不足,但柴可夫斯基非常注重個人衞生,而且他地位顯赫,生活條件優越,然而卻感染霍亂致死,令人懷疑其死因另有別情。
更可疑的是,由於擔心傳染,以往霍亂患者的屍體會被嚴格隔離,但柴可夫斯基的遺體卻被公開展示,供人瞻仰,來送別的人當中,甚至有人親吻死者的臉。
遺體公開展示
此外,柴可夫斯基的住所在他離世後並沒進行消毒,床單也沒銷毀而是送到洗衣房清洗,這些都與當時處理霍亂死亡人士的標準方式有所不符,令人更加覺得不尋常。
柴可夫斯基的健康狀況一直不佳。他從小體弱多病,14歲時母親因霍亂去世,對他造成極大心理創傷。成年後,他長期受腸胃問題困擾,還有失眠、焦慮和抑鬱,有傳聞這可能與其性取向有關;當時的俄羅斯社會,同性戀被視為嚴重道德缺陷,這對柴可夫斯基造成重大壓力,他不愉快的婚姻更導致他嘗試投河自盡,令他有斷袖之癖的傳言更加熱烈,可想像壓力有多大。

關於柴可夫斯基的死因,流傳着另一種說法:自殺。1979年,蘇聯音樂史學家亞歷山德拉奧勒洛娃(Alexandra Orlova)提出,柴可夫斯基因同性戀醜聞驚動皇室,被8名帝國法律學院舊同學組成的一個名為「榮譽法庭」判處他自殺,以保護他和皇室的名聲,柴可夫斯基因而服下砒霜,引致霍亂症狀(腹瀉、脫水、急性腎衰竭)後離世,以掩蓋真相。奧勒洛娃將她的研究寫成一本書,但遭前蘇聯禁制,直至1990年翻譯成英文才得以印製出版。支持自殺理論的證據還包括:他在去世前幾天情緒低落,並在《第六交響曲》中寫下極具悲劇性的終章,被許多人解讀為「告別生命」的暗示。

解封防疫措施
此外,柴可夫斯基的醫生瓦西里伯頓森後來承認,從未治療過霍亂病例,這讓人懷疑他的診斷是否可靠準確。換成今日,我們對確診霍亂當然有信心得多,不論細菌培植抑或核酸檢測,都能查驗到大便裏有沒有霍亂弧菌,還可以細分它的血清型,分辨是否導致霍亂爆發的O1和O139型。O1和O139霍亂弧菌感染在香港是須呈報的傳染病,2024年全年只有兩宗個案,都是從外地輸入,可見高爆發風險的霍亂在現今先進的香港並不常見。
細看柴可夫斯基的自殺理論,當中亦有不少漏洞。在霍亂檢疫方面,自從1892年春天俄羅斯發生霍亂以來,1893年11月已是第四波,相信當時俄羅斯政府已累積相當的經驗應付霍亂。1893年4月出版有關霍亂防疫的法則中,已再沒禁止舉行人數眾多的大型出殯儀式。現時已確切知道,感染霍亂需要大量霍亂弧菌才能致病;參加喪禮並不會傳播霍亂,就算接觸或處理死者屍體,只要在接觸後做好手部衞生,便不會有感染風險。所以,當年俄羅斯政府改變防禦措施是合理做法,慢慢逐步解封,情況就像新冠疫情一樣。
死前計劃新作
另一方面,柴可夫斯基在生命最後幾周和朋友的書信中,並未表現出絕望,反而計劃未來的新作品;他的弟弟莫德斯特也否認自殺的說法,堅持霍亂的解釋。此外,沙皇亞歷山大三世對柴可夫斯基的死表示哀悼,並親自支付葬禮費用,這表明官方並未因他的性取向而排斥他。
無論真相如何,柴可夫斯基的死亡,突顯十九世紀傳染病對社會的影響。霍亂在當時被視為「窮人的疾病」,因此上流社會對柴可夫斯基的死因有所質疑,他的案例也反映了當時醫學的局限性,診斷可能出錯;此外,社會對同性戀的污名化,可能加劇了他的心理負擔,間接影響其健康。
柴可夫斯基的葬禮規模盛大,超過6萬人申請參加,最終有8000人擠進喀山大教堂。他的音樂至今仍深受喜愛,而他的死亡之謎則成為歷史學家和音樂愛好者持續爭論的話題。無論是霍亂還是自殺,他的離世都標誌着浪漫主義音樂時代一個重要篇章的結束。
撰文 : 王建芳醫生_臨床微生物及感染學專科醫生
[信健康] 揭開柴可夫斯基之死,醫生資訊派上場!【更多健康資訊:health.hkej.com】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