步入生命晚期 尊重病者權利 家人放下糾結 靜心應對如何善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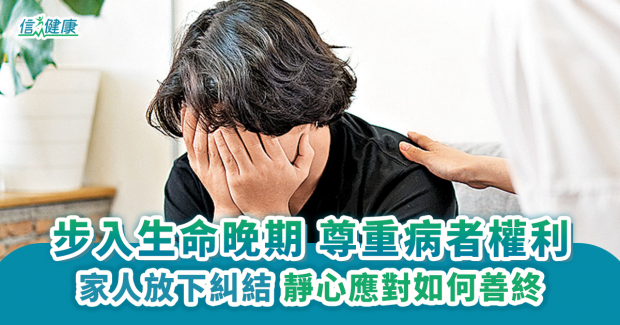
上月底應邀在「毋忘愛」社區生死教育講座「死亡咖啡室」(Death Café)作短講和對談。這是一個提倡自主管理臨終計劃的非政府組織,有一系列與生命晚期相關的服務。我在現場與聽眾一起思考的主題是:家人在病者臨終時期的醫療決策上擔任什麼角色?在生命晚期,尤其當病者接近臨終階段,往往面對複雜的醫療決定。病者、親屬、醫生之間有一種微妙三角形關係互動,大多時候是良性,但也可能出現緊張和糾結。
法律和醫學倫理的原則並不複雜:無論在生命哪一個階段,除非病人已經沒有精神能力自主,為尊重病人自主和個人權利,醫生與家人應該盡力讓病人知情,按照其意願作出醫療決策。當病人沒有精神能力自主決定,家人可能成為主要決策者(例如作為法定監護人),但仍必須基於病者的最佳利益(Patient's best interests),而非由家人自己的價值觀主導。
多重角色複雜關係
複雜的是,現實中的生命晚期情景並不是一個純粹的理性空間。家人的角色往往同時是不同程度的決策者、照顧者、哀傷者。「簡單」決策例如是否要病人接受用鼻胃飼管餵食(Nasogastric tube feeding)代替進食;沉重決定例如是否預先拒絕施行「心肺復甦術」(CPR),對身兼多重角色的家人是很大的挑戰。放開自己情緒,設身處地按照病人自己取向做決定,並非容易的事。況且一個家庭可能早已在長年累月中形成特定的互動模式,其中隱藏着成員在重大決策上面的權力關係。
無論親近與否,在家人和病者之間也可能出現「糾結」(Enmeshment)。這概念源自家庭治療師Salvador Minuchin(1921-2017)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提出的理論,最初用以解釋,在某些家庭,模糊的個人界限於糾纏不清的關係中如何扼殺個人健康成長和發展。當家庭成員過度參與彼此的情感和生活,不健康的緊密關係會導致個別成員失去自主,個人與家庭交織,你中有我,我中有你,成員難以好好表達自己意願。
在生命晚期的情景,「糾結」或者會表現在幾方面:
一、界限模糊:過度介入醫療決策,無視病人的自主意願,甚至強迫醫生接受家屬的選擇。
二、情緒主導:出於焦慮,要求不必要的治療或阻止醫生告知病人真實病情。
三、溝通失衡:家屬與醫生直接溝通,排除病人參與;或三角化溝通,家庭內部矛盾透過醫生傳話,使醫生陷入家庭衝突中。
前面提到,在病者生命晚期,家人往往同時是決策者、照顧者、哀傷者,多重身份有時會導致決策上的認知偏差。
首先是「拯救者偏差」:個人接受不了病者的病情將無可避免地持續惡化,不能放手,堅持透過積極治療以緩解自己的無力感,即使這樣可能延長病者痛苦;其次是「愧疚驅動」:不知不覺試圖用醫療手段補償自己未盡的情感責任。
預設醫療指示助溝通
因此,病者、家人和醫生的三角形關係,家人的糾結可能令理性受壓,導致不盡符合倫理原則的決策,損害病人的自主權和利益;另一方面,醫生在醫療上可能偏重技術,着眼於狹義的干預成效,忽略了晚期至臨終的醫療決定底下有人性和社會性因素。即使醫生自己無意(或者因為沒充裕時間)了解家人和病者的糾結,他也有基本責任協助病者與家人了解各種選擇的利弊,促進良性互動,盡可能尋求共識。

每個人都有一天成為病者,最終步入生命晚期。現代醫學愈強大,「如何善終」的考量愈見複雜,需要靜心應對。讓病者生命的最後一程能夠有尊嚴、受尊重和身心安寧地走完,照顧上必須兼備真實的關懷與嚴謹的倫理。家人是病者情感的核心支柱,他們的陪伴、傾聽以至擁抱,有無可替代的支持力量。然而,照護者的身心壓力、感情糾結,在在影響醫療決定的合理性。尤其當病情轉壞,家人心急如焚,很難即時理解倫理的界線和原則。
可喜的是,香港社會近年打破忌諱,可以更從容地談論死亡和預早規劃生命晚期的醫療和照顧。去年底政府為「預設醫療指示」立法,促進病者自主,是一個重要里程碑,民間也見不少有心人跨界別推廣「預設照顧計劃」,可以成為訂立預設醫療指示的基礎,也適合其他有嚴重健康問題而未能自主的病人。家人參與,預先做好溝通,可以讓關懷與倫理並行,避免臨危才急遽地作出粗疏的決定。
(本文屬作者個人意見,不代表中文大學生命倫理學中心立場。)
撰文: 區結成醫生_中文大學生命倫理學中心顧問
[信健康] 應對生命晚期者關懷,倫理資訊要留意!【更多健康資訊:health.hkej.com】




